殺人狂魔或病人?人神共憤判決背後的大坑
撰文/公民人權協會調查研究小組
近日新聞排山倒海說,為了社會安全,為了減少精神障礙者再犯下暴力傷人,甚至殺人的行為,送他們去精神科醫治。CCHR公民人權協會基於全世界三十五國,五十年的研究為基礎,我們要說,這樣的安排注定失敗。
這不是唱衰,這大概是最誠懇的忠告。

令人髮指的犯行,傷人奪命
殺童割頭的曾文欽和王景玉、殺害台中牙醫的賴亞生、恍惚刺殺人的王巧豔、火車站殺警的鄭再由、隨機殺人王秉華,他們被認為的共通點是有精神障礙病史。但是精確的說,他們都曾經是精神科的病人。
曾文欽,2012年12月1日,在遊樂場將國小五年級男童割喉致死。從2004年到案發,有接受精神科治療,警方還從住處搜出許森彥精神科診所藥袋,當時他還在吃使蒂諾斯、贊安諾和抗焦慮劑舒神。
王景玉,2016年3月28日捷運站旁砍掉四歲小女孩的頭。從2010年到2016年10月,曾數次被警消分別送過三軍總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接受治療。曾經沈溺毒品長達6年,也有暴力攻擊行為。
賴亞生,2018年5月24日持刀血洗台中牙醫診所。2010年到2015年,在維新醫院接受治療六年,曾被開立抗精神病藥物氯氮平。
王巧豔,2018年5月25拿刀捅人。2016到2018年初有治療,吃抗焦慮劑。過去無暴力前科,亦無暴力傾向。
鄭再由,2019年7月3日在火車上用刀刺死年輕警員李承翰。2010年到2017年2月在奇美醫院精神科看門診,後持續拿慢性處方箋,服藥史有十年。
王秉華,2020年3月13日在新店捷運站隨機刺死路人。2009年國中時就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專思達,成年酗酒吸大麻,案發時他也正在看診、服藥。
屏東挖眼楊姓男子,2021年9月26日痛毆並挖女店員雙眼。十年前就有傷人前科,也被送精神科治療,2021年6月拿刀攻擊老婦再度送精神科強制就醫,8月14日出院。
令人髮指的犯行,傷人奪命,引發社會恐慌,但這還不夠,幫被告辯護的律師,以及法院判決,都會搬出刑法第19條〔註1〕或人權兩公約〔註2〕。引發殺人卻無罪的人神共憤判決。
現在政府解決方案及立法院一面倒,認為鋪開社會安全大網,一定要從投入更多資源給精神病學,以精神病學為解決方案。CCHR公民人權協會舉出以上案例,想說明一個事實,很多暴力犯罪者,曾接受精神科治療,甚至長期治療,最後仍無法阻斷悲劇發生,是精神科和精神病學沒有辦法處理暴力犯罪的證明。
精神病學能處理暴力犯罪?
引用立法委員陳柏惟在臉書上發表的言論:「根據統計,所有犯罪者中,15%的人在過去一年內,27%在犯罪之前的人生中曾經使用過精神醫療服務,這雖不一定和他的犯罪有關,但若能在此時確實施予治療,則未來的暴力危險便能大大降低。」
我們要說,陳委員,您的推理不盡正確,因為曾文欽、王秉華在犯案當時,都接受精神科治療,都在吃藥。但是如果陳委員說「犯罪者中,15%的人在過去一年內,27%在犯罪之前的人生中曾經使用過精神醫療服務」為真,那再度證實,精神科治療和減少犯罪真是無關。反而,精神科治療跟犯罪的上升有沒有關係呢?藥物副作造成憤怒、幻覺和斷片,有沒有可能才使人更容易暴力犯罪?這個主題迫切需要治安單位深入研究了解。
CCHR公民人權協會的共同創始人精神病學博士湯瑪斯.薩茲教授(Thomas Szasz)對精神科摻合司法判決這件事,相當反對。
薩茲博士說:「我認為應該廢除精神失常辯護,這個批判一部分基於學理,另一部分基於實務考量。在學理上,非常簡單地說,精神失常是一個有爭議的用語,它可以指兩件事:第一是腦部疾病…第二種,是不良行為。…疾病,腦部疾病,不會導致犯罪行為。癲癇作為一種腦部疾病不會導致犯罪行為。癲癇患者可能會也可能不會犯罪,就像其他人一樣。」
的確,生病的人值得同情,但是,沒有法官會因為一個癌症患者說「痛到不能控制情緒」而砍了護士,或是甲狀腺亢進患者突然憤怒的失去理智傷人,便可以判他們無罪,不可能。那為什麼精神障礙卻可以?或許,為精神障礙辯護或精神鑑定,是司法系統裡,巨型的詭辯大坑。
刑法十九條的坑愈挖愈大
把「不當行為」甚至犯罪當成精神障礙,會有什麼問題呢?薩茲博士說:「精神失常通常是在一個人犯罪之後決定的,通常是在某個事件造成社會不安之後。」這些話是他為上世紀的美國說的,但是也相當符合台灣現狀。刑法十九條為精障者辯護的條文,近年被拿來擴大為吸毒的殺人犯和沒有任何精神病史的人辯護,實在蔚為奇觀。
例如殺了四位民眾的鄭捷並沒有精神病史,而辯護律師不斷主張鄭捷需再次進行精神鑑定(當然那是律師的職責)。拿刀連砍媽媽37刀,並剁下頭顱丟到社區中庭的吸毒梁男,二審還認為他吸毒「欠缺辨識行為能力」,2020年8月判決無罪,輿論根本炸鍋,網友怒罵司法體系得了思覺失調。今年八月中,還有個開野馬跑車超過時速100公里,闖紅燈撞死21歲女騎士的葉姓嫌犯,他的辯護律師主張葉有精神疾病,要求送醫鑑定。看到這些新聞,有正義感的人拳頭都硬了。裝睡的人叫不醒,裝瘋的人演不停?
從政府,立法委員到民眾,對精神科能發揮的社會安全功能,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這可能是精神病學引導人們這麼想,然而只有「宣稱」,但是完全沒有實證。如果精神科真的對社會安全有效果,我們看統計數字顯示,接受治療的精神科門診患者,從1998年150萬人,每年增加,到2019年已擴展成280萬人,那麼我們的社會應該比二十年前更安全。但是並沒有!

精障族群背黑鍋
還有更糟糕的效應。因為這些社會案件,媒體的報導和精神科的發言,似乎都有意無意的,把精障患者和犯案者綁在一起,劃上等號。雖然總有精障人權團體大聲疾呼,不要污名化精障者,但是,每一回為精障犯罪者辯護無罪、減刑的新聞,每一回倡導把精神治療當成解決社會安全的議題;卻更把精障患者和犯罪者打包成同一個物件。每發生一次慘案,這個印象就被強化一次,加深一次。
為什麼?因為精障患者無罪和減刑的遊戲規則不公平,這個遊戲規則製造了一種社會衝突,而衝突吸引了大眾目光。這個等號被愈劃愈深,偏見和歧視的人性缺點,也被深挖成另一個巨坑。最後背黑鍋的,是與犯罪無關的精障族群。
曾經在花蓮署立玉里醫院精神科病房住了十八年,花了十年時間自學本身的法律權益,終於把自己救出精神科病房的盧博熙,談到他在精神病房裡遇到精障犯罪的遭遇。順帶一提,從過去以來,就現有的制度,精障罪犯都有受到精神科的治療,罪行重大的留在特定的監獄,評估之下不那麼危險的罪犯,會送到醫院的精神病房。
盧博熙表示:「花蓮署立玉里醫院,2600多人裡,有20-30位是罪犯被關在那裡。有一次這個罪犯攻擊人,搶東西,當時我們四,五個病患防禦性的制伏了那個罪犯,卻被醫院當成是圍毆那個罪犯。醫院處罰我們,關隔離室。
那種人是蓄意,惡意的搶人手上吃的,我有次抽菸,菸被搶走。他還會用鏍絲起子戳別人太陽穴,或是用筷子戳人眼睛。跟這樣的罪犯睡在同一個房間,真的很危險。」
「精神科醫生一直為這種殺人犯辯護,為犯刑法的罪人辯護,然後污名化普通病友「有犯罪可能」,是基於什麼心態?精神科跟他們這些人是同一國嗎?那叫精神科醫生跟這些罪犯睡同一個房間啊!」

(照片資料來源:蘋果新聞網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10930/PMW3X4KQCVAYDANJZ6DRUBAYDU/)
精神病患,是社會上的弱勢,絶大部分的人也怕罪犯,或說比一般人更怕他們。盧博熙補充:「我在精神病院裡待了這麼久,99%的精障患者,如果你不去激怒他,並沒有什麼傷人的暴力傾向。真的沒有必要把兩件事情混為一談。
犯罪者如果要處監護處分五年,該放專責病房,或去一般監獄。」
把精障犯罪判無罪的始作俑者
也許始作俑者是那位打開「精障犯罪無罪」之門的美國法官。1954年,美國法院的主審法官大衛貝茲倫(David Bazelon),曾在法庭上推翻了一個有罪判決,然而那段期間,貝茲倫下班也正好在做精神分析治療。犯人蒙特達拉謨(Monte Durham)雖然有長期犯罪記錄,但他堅稱自己有精神障礙,所以不知自己幹的好事。案子到貝茲倫手上,他推翻了之前法官的刑事有罪判決,把精神科證詞引入法院,從此法院門戶大開〔註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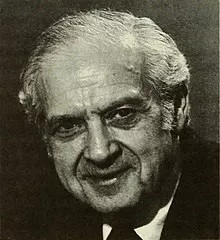
(法官大衛貝茲倫David Bazelon)
事情開始於美國的司法體系,並進一步衝擊、外銷到全球。全球法學已對「精神異常到心神喪失、無法辨別現實的人,就沒有辦法負擔責任」這個論點照單全收。如今台灣司法界,把持著精神鑑定的精神病學,也儼然成為刑事犯罪的白袍法官。
然而,就是這個論點「精神異常到心神喪失的人,就沒有辦法負擔責任」製造了判決最大的亂度,導致每次一碰到精障犯罪,媒體和輿論就吵成一鍋粥。因為法官判刑,需要一刀切的判斷「有能力」或「無能力」。但是我們看到精神病學,常常不同的精神科醫生面對同一位病患,卻發生診斷或精神鑑定不同結果。更別說精神疾病被他們自己搞得極為複雜。有沒有能力,理不理性,被形容如光譜表現,只有漸層,沒有一刀切。因此判刑扯到了精神障礙,馬上疊加摻雜精神病學特有的武斷。因為精神科到現在,還未發展出可靠客觀的生化檢查和能重複驗證的鑑定系統。
大家也都知道,精神病學其中一個特色是,談到疾病成因,常常講不清,說不明白,精神科醫生自己也承認,醫生的經驗、距離案發時間、接收的資料整合等因素,都可能出現鑑定差異。這樣子的醫學,政府和民眾要怎麼期待它解決「社會安全」問題?信賴基礎究竟是什麼?畫大餅很容易,然而實際成效在哪裡?
精神病學對暴力、殺人犯的管理,有何具體貢獻?
在台灣的精神病學界,其實不少精神科醫生也覺得淌這個司法精神病學及鑑定工作,其實吃力不討好。夾在維護精障者人權與社會安全之間,也多感嘆不容易。果真如此,精神病學實在該誠實並大方的承認,精神醫療並不是社會安全網的關鍵要素,也沒必要做出有把握能扭轉乾坤的樣子,導致政府和社會大眾有所期待。畢竟,沒有研究或實證指出,精神病學對暴力、強姦、搶劫和殺人犯的管理,有過什麼具體貢獻。
面對目前這個司法難題,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副理事長劉承武提醒法律界人士,要堅持住兩條界線:
「一、這個人的精神疾病是因為『反社會人格違常』而發生的嗎?二、他本身的精神疾病是自行招致的嗎?〔註4〕
精神衛生法第三條有提出〔註5〕,要排除一項東西,叫做『反社會人格』。這個部分就不是精神疾病,因為他是先有反社會人格之後,才形成精神疾病。這時候不能列他為精神疾病,否則每一個反社會人格,最後都變成無罪,社會就天下大亂。……所謂的精神疾病,還不能因為自己故意或過失而招致的精神疾病。
什麼叫過失?客觀上認為,我預見我有可能發病,我竟然放任無所謂的態度、容許的態度,讓我自己引發精神疾病而殺人,這就是因過失而自行招致,這時候不可以免責。否則每個人都用這種方式,那台灣還有安寧、安全、安靜的可能性嗎?就沒有了。」
既然反社會人格違常不包括在精神病,不用搞複雜的精神鑑定,那麼我們非常期待法官都有能力判斷出來,並且一刀切。相信守法的精障患者也非常樂於跟反社會人格違常者和罪犯從此分道揚鑣。
對於精障犯罪的問題,盧博熙有自己一套看法:「思覺失調病人殺人傷人的事情,千念萬念其實都在一念之間。這些殺人犯,就應該用刑法來判刑,不要扯到精神病患的大傘之下。個人造業個人當。如果精神真的異常到心神喪失、無法辨別現實,那他們為什麼砍的是「人」,而不是機車或樹呢?沒有人覺得這很奇怪嗎?」

讓罪犯回歸刑法,這可能是衝擊法學的另類觀念,但如今正是我們全面檢討精障犯罪辯護的利弊得失之時。就像精神病學薩茲博士所說,「對違法者不罰,等於是對守法者的欺騙。違法者應當受到懲罰,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認證守法行為是好的,推崇守法行為的價值。刑法的目的不能只是矯正或嚇阻;維護法律秩序才是它唯一的宗旨。」「所有犯罪行為都應該用刑法來管控,不該讓精神病學參與執法。」
聰明的讀者或許會問一個問題,如果精神醫療不是社會安全的關鍵所在,那什麼才是呢?也許參考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口號:「愛的相反不是恨,愛的相反是冷漠」、「關心別人就是保護自己」。對社會的疏離分子應當給予主動關心。在疏離分子的人性被完全冰凍之前,用我們的人性去融化他們,使他們變成柔軟。對於已經犯罪的人,用刑法維持這個社會應有的秩序、公平、正義。這樣的社會,才能對被悽慘傷害的守法者、死去的好人,以及普羅大眾有一個交待。
〔註1〕刑法第19條: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註2〕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縮寫為ICCPR)在1966年由聯合國第2200(XXI)號決議通過,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縮寫為ICESCR)合稱為兩公約,在1976年生效。台灣於2009年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
詳見:https://covenantswatch.org.tw/un-core-human-rights-treaties/iccpr/
〔註3〕“Rebinson Remembers 30 Years of APA,” Psychiatric News, 16 Nov. 1979.
〔註4〕反社會人格違常:節錄自立法院法制局研究「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文章: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往往缺乏道德觀念,缺乏罪惡感,情感不成熟,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其特徵行為是以衝動和不負責任的方式,有時是以敵意和嚴重暴力來顯露內心衝突。他們對挫折的耐受力很差。常不能預計自己的反社會行為帶來的消極後果,絲毫沒有不道德或罪惡感,極力反對任何以改善為目的的活動或團體。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171394
〔註5〕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一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